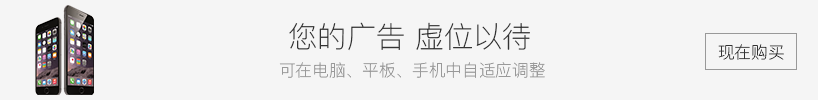老于打过日本鬼子,这是三里五乡尽人皆知的事。据说当年因作战勇敢还在太行军分区的一个纵队里当过连长、排长啥的,光军功章就有好几枚,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别人问起老于以前的事,老于总是打个哈哈就过去了,避而不谈。
老于身材高大,腰杆笔直,一脸义正辞严的严肃架势,虽然岁月的风霜已经爬满了面颊,头也有些微微的谢顶,可行走坐立还是透着那么一种凛然的军人气质。老于老伴儿去世得早,也没能给他生养下一男半女,因此一直一个人独居生活。好在有村委会的照顾,时不时找人帮助他洗洗涮涮做做家务什么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老于的老伴儿是***后期去世的,老于觉得老伴死得早,和整天跟着他担惊受怕吃苦受累不无关系。那时老于被扣上历史***的帽子,说他参加过***,抗日时还私自放跑过一个日本兵。日本人在咱中国杀人放火,放跑日本人那不是***是什么?
那几年,老于为这没少挨批斗,公社和村里的大小批斗会他必须都得参加,不是被批斗的主角就是陪绑的对象。他头上带着高高尖尖的纸糊的白帽子,脖子上被强挂上大牌子,大大的红叉把***于得水的名字分解的支离破碎。每次参加批斗会,老于都会雷打不动的穿上他当年那身土黄色的旧军装,一脸严肃,不卑不亢,好像是去参加什么重要的军事会议。态度始终是不申辩、不搭理、不认错。有时中学的***来批斗他,拳脚和皮带挨上几下也是免不了的。***那几年,他和那些地富反坏右们一起被监视着劳动改造,在村子里扫大街、清理厕所、出圈肥,净干些脏活、累活,受尽了屈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日本的旅游团到河北旅游,其中一个团成员找到县民政局,要求帮助查找当年八路军太行军分区某团的一名战士,并且说这个战士曾经救过他父亲的一条命,这次是受他父亲的委托,当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来了。县民政局不敢怠慢,通过他提供的一些信息和特征,翻阅了许多资料,多方查证,辗转找到了于得水。当这个日本旅游团成员见到了于得水,拉起了他的手,激动的大叫起来。老于相比起来倒是显得很平静,他承认,他在和日本军队的最后一次作战中,的确救过一个年轻的日本兵。
那是1945年的7月底,距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军部署了一次军事行动,对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扫荡,上演了最后的疯狂。那是一次非常惨烈的战斗,在巍巍的太行山脉纵横的褶皱里,敌我双方从近午一直拼杀到日暮时分。残阳如血,硝烟弥漫,尸横遍野,一片狼藉,近200个鬼子和伪军被老于所在的八路军某团消灭在荆棘遍布岩石嶙峋的山谷之中。向晚,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停息下来,终于归于沉寂。八路军来不及打扫战场,奉命迅速转移撤出了战斗,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敌人的援军正向这里搜索而来。他们利用短暂的战后间隙,救治了受伤的同志,简单的捡拾一些遗弃的枪弹,就迅速的转移了。老于走在了最后边,他心里打着一个小算盘,还想着找一双合脚的敌人的皮靴,因为他的那双布鞋,在近几个月的翻山越岭与敌周旋中已经磨烂了,鞋帮绽裂,鞋底漏出了脚后跟。
老于在敌人的死尸中翻找,见到皮靴就扒下来看看,不是瘦的夹脚,就是沾满了血污,没有满意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双还算可以的,换好了鞋,正打算离开去追赶队伍,就听到不远处的岩石后面的草丛里有动静。他悄悄走过去绕到岩石后面,用汉阳造步枪拨开草叶一看,只见一个年轻的日本兵瑟缩的蜷曲在那儿,看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一脸稚气。侵华战争后期,日本兵员严重不足,为支撑侵略战争,把十几岁的少年也驱赶到战场上充当了炮灰。老于举起了步枪,雪亮修长的刺刀上闪着逼人的寒光,日本兵稚嫩的小脸上充满了惊恐,浑身因害怕而瑟瑟发抖,绝望的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老于犹豫了一下,刺刀终究没有扎下去。他轻轻叹了口气吆喝一声,手伸到怀里摸索着。日本兵听到声音睁开眼睛,看到右手虎口有一个大黑痣,满是烟熏的手中拿着一个金黄色的玉米饼,伸到了自己的眼前。他哆嗦着用双手接了过去,然后埋下头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老于转身离开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老于又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因作战勇敢,上级领导也非常重视他,准备提拔使用,但因为性格直,说话得罪了人,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揭发当年还曾私自放跑过一个日本兵,这可是一个政治事件,部队***也没办法,就借着精简机构的名义,给他办理了退伍还乡手续。
这个日本旅游团成员执意要给老于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为了了却他父亲的一个心愿,也作为这么多年来他辛苦的补偿,但被老于拒绝了。老于说,如果实在要给你就捐给村里的希望小学吧。
日本旅游团成员临走时,要老于写段话带给父亲,老于提笔郑重写下了八个字“勿忘历史,珍爱和平”。